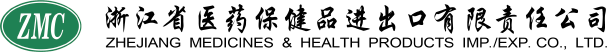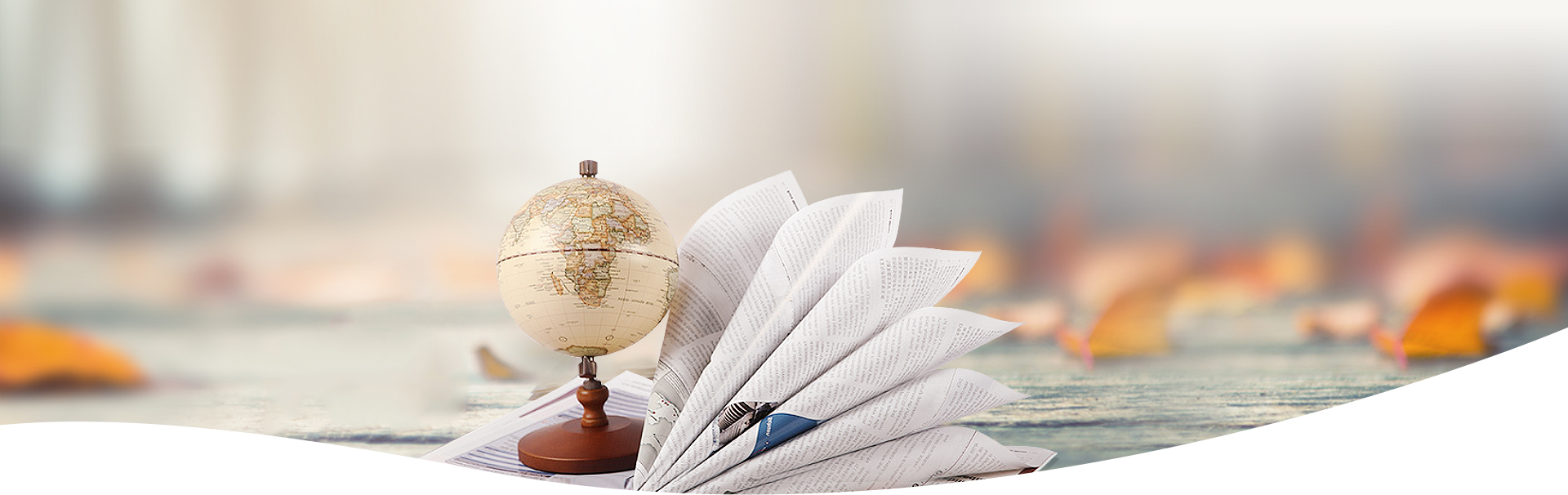多乐游戏中心: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1月10日公布消息,公布了对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春良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调查情况。
指出其在任期内“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公司经营、项目承揽、行政许可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2016 年 12 月,李春良 “空降” 出任国家林业局(2018 年改组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并自 2017 年 6 月起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主任,直至离任。
他深度参与了首批国家公园的设立、规划和管理工作,分管国家公园建设、自然保护区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核心领域。
2022 年 7 月,李春良因年龄原因被免去国家林草局副局长等行政职务。
巧合的是,就在李春良进入国家林业系统的同一年,林业部门不再向外界公布穿山甲的库存数量。
根据2008—2015年七年的公开数据统计,全国总消耗控制量约为186吨,平均每年26.6吨左右。
穿山甲甲片入药在我国一直都处于合法状态,最新版的中国药典中有8种中成药含穿山甲片,包括用作活血通络的「再造丸」和缓解脘腹疼痛的「阿魏化痞膏」。
另外,卫生部及国家药品监管局还批准了72种含穿山甲片的专利处方,也就是说,在我国,官方允许售卖的药品中,至少有80种含穿山甲成分。
据统计,目前至少有221间制药企业及713所医院可以生产或销售含穿山甲片的中成药。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穿山甲甲片入药”背后是一个巨大的穿山甲药用市场,穿山甲贸易由此繁荣。
据美国环境署(EIA)的统计:中国共有56家制药企业和相关第三方网站上宣传了总共165种穿山甲片的药物产品,生产这些药品的公司包括中国最大的中药企业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附属公司遍及全球,其中亦有欧美投资的企业。
另外,还有非常多含有穿山甲成分的药品作为一些民间偏方在更隐秘的地方,通过更隐秘的途径售卖,或者是难以被统计的线下穿山甲药品。
除此之外,含有穿山甲成分的药品甚至还被纳入医保,包括:威灵骨刺膏、再造丸、拔毒膏、茴香橘核丸及痔血丸。
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 简称UNODC)的报告,穿山甲是世界上被贩运最多的哺乳动物。
2014年至2018年间,查获的穿山甲鳞片数量增长了10倍,相当于每年141,000 只穿山甲。缉获的穿山甲鳞片多数用于传统医药,主要目的地是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
尽管穿山甲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且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出售、购买和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但“因科学研究、人工繁育、公众展示展演、文物保护或者其他特殊情况”的除外。
而药企就能够准确的通过法律所规定的“特殊情况”,在“依规定取得和使用专用标识,保证可追溯”的情况下使用穿山甲鳞片生产药品。
上述条款中的“专用标识”指的就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专用标识。
国家林草局名下的“野生动物研究与发展中心”是国内所有“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的供给单位。
虽然按照理想情况,此“专有标识”的攻击单位——国家林草局,可以对野生动物制品来源进行统一溯源,确保来源合法。
但在实际操作中,林草局并没有对来源进行一一核实,EIA于2020年针对中国穿山甲贸易发布的深度调研报告显示:
这意味着国家林业局无法核实所批核作商业用途的穿山甲片之来源地。这也表明了 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制度未能发挥其声称功能,确保能追溯制药企业所用穿山甲片的合法性。
从制度设计的初衷来看,野保标识应当是保护体系中极为关键的一环——它代表“合法来源”的背书,也是公权力介入野生动物贸易的核心接口。
然而,当标识无法起到它所应发挥的作用,它便不再是保护的象征,而有几率会成为利益合法化的工具。
我国的药品制造公司有两种渠道可以采购穿山甲鳞片:经过验证的政府库存和穿山甲繁育中心。
虽然人工培育穿山甲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但目前所有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因此,实际上只有政府库存的穿山甲鳞片才算合法来源。
根据EIA的调查,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统一的全国穿山甲甲片库存管理体系。“2006年,所有持有穿山甲鳞片库存的个人和私营企业向相关省级林业部门申报其库存收购数量和时间。林业部门随后被要求对私人持有的库存进行全方位检查和核实,并向国家林业局报告,从而形成了国家合法库存。”
现在让我们回到前文关于李春良上任后穿山甲甲片库存数量成谜的问题,展开聊聊这到底对穿山甲贸易有何影响。
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进行说明:假设国家穿山甲甲片的合法库存一年只有1吨,而所有药企的实际的需求为2吨,那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有1吨的穿山甲甲片缺口,有部分药企不足以满足需求。
这种情况下,需求未得到满足的药企就非常有可能通过非法的手段获得穿山甲甲片,比如从国外走私、在国内非法猎捕穿山甲。
而当合法库存的具体数量对公众与媒体不透明时,这些非法来源的穿山甲鳞片就更容易披上“合法”的外衣——只要能拿到“专用标识”,就能顺利流入市场。
2020年12月17日,据裁判文书网披露,三和药业及7位股东、员工因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获刑事处罚。案件显示,2016年至2018年间,该公司以2.9亿余元的价格非法收购穿山甲甲片9890公斤,并以4531万元的价格销售给包括亳州珍宝岛中药控股有限公司、源和药业、江阴天江药业等在内的6家公司。
这些买家背后涉及多家上市公司:江阴天江药业为中国中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一方制药同样由中国中药间接全资控股,而亳州珍宝岛则系A股上市公司珍宝岛药业的子公司。
为了让这些非法收购的穿山甲鳞片获得“合法身份”,三和药业股东陈某银上演了一出“空城计”:
他们在向野保部门申请行政许可时,用空箱或白芍替代穿山甲片虚增库存数量;野保部门工作人员检查时,仅抽查表层几箱,便贴上封箱单发放许可;
更荒谬的是,三和药业还花费12万元伪造了10万枚虚假野保标识,将其作为“合法凭证”使用。
根据EIA的调查,目前我国并没有穿山甲片需求量的最新资料, 但历史资料显示在1990至93年间,一家制药企业曾收购 70吨的穿山甲片;仅在 1991年我国政府就进口了63吨穿山甲片。在2002年,以穿山甲片入药的总量达80-100吨。
以 2008至2014年间穿山甲片被公示的合法库存计算,供应远远不能够满足市场所需。
调查进一步揭示,当穿山甲甲片供不应求时,穿山甲贸易就催生出政府出售或从全球非法供应链购买的灰色利益链条。
2021年林草局发布的《罚没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保管处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里有相关陈述:罚没的野生动植物制品能够最终靠“公开拍卖”的方式处置。
更早之前,李春良空降林业系统当高官的那一年,也就《处置办法》出过征求意见稿,其中也提到了“公开拍卖”。
如果你简单地检索一下网上有关查获穿山甲走私案件的新闻报道,就会惊奇地发现,这些报道里面根本不会提到被收缴的甲片到底去了哪里。
据统计,在2010-19年间,我国警方缉获了至少67.5吨穿山甲片 ,可是涉案物品最终如何储存及处理,却并没有向公众交代。
2013年,安徽省林业局委托省内一个企业拍卖涉案的穿山甲片,最终拍卖成交价147万人民币(约20万美元),2019年,一份来自安徽省林业局的批核文件显示,两家制药企业分别于2018及2019年获批准交易被「查没」和「拍卖」的库存 。
虽然政府官员曾公开表示,遭查没的穿山甲片会按情况销毁 ,但以上例子却证实涉案的鳞片已流入商业买卖的供应链,而此供应更有可能从未间断。
购买政府收缴的甲片还不够只是一种来源途径,此前,某环保组织曾通过秘密调查发现,国内有野生动物贸易公司透过国际供应链采购穿山甲片并售予药企。
有航空运单显示一家公司于2018年销售了两吨穿山甲片,安徽省林业局文件中也有这宗交易的记录。
而该公司曾于2016年从一个非洲国家进口数吨穿山甲片到中国 。该公司于2018年出售的鳞片有很大的可能性就是来源于2016年进口的同一批货品。
事实上,在国内关于穿山甲贸易已形成了这样一种诡异的模式:林草局发证——药企通过走私等途径“自由”交易买卖——“合法”流入市场。
国家林草局副局长李春良被爆出的以权谋私,不得不让公众更加警惕野生动物非法贸易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当拳力缺乏监督、信息不够公开透明、公众被隔绝在数据之外,“保护”便有可能异化为“利用”,“监管”也可能变成“寻租”。
穿山甲只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案例。一个被誉为“地球上最古老的哺乳动物”,在国际公约中被列入最高级别保护名录的物种,却在合法的制度缝隙中被残忍买卖。
从“库存成谜”到“标识失真”,从“拍卖罚没物”到“进口灰色链条”,每一道本应承载着监管与保护的程序,都在权力与利益的交易中,被逐渐做空。
当我们反思这场“以权谋私”的悲剧时,也该重新审视制度怎么样才可以回归公共利益。
在此,郑重呼吁恢复穿山甲等濒危物种库存与交易数据的公开,建立第三方独立监督管理机制,限制行政许可的拳力空间,让社会、媒体与科研机构能够共同参与监督。
世界的改变,不是因为少数人做了很多,而是因为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向“善意”的方向,迈一步!让我们一起分它一口,改变它的命运!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